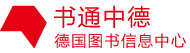媒体中心

故事的力量
《新知》杂志,陆晶靖, 1999年11月30日
上帝需要故事,所以创造了人类——艾利•威瑟尔
故事就像天气。关于它,谁都能谈论点儿什么,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属于极易了解但难以深究之物。伦敦奥运会闭幕式的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说:“故事没有规律。”他还是电影《时时刻刻》和《朗读者》的导演。同是电影界大腕,好莱坞编剧大师麦基不这么看,他写过一本书就叫《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制作的原理》,里面不厌其烦地讲述各种构造故事的方法和窍门,他说“自两千三百年前亚里士多德创作《诗学》以来,故事的奥秘就就如同大街上显眼的图书馆,众所周知”,他所做的只是把这些奥秘再讲一遍。这两人的分歧产生于看问题的角度:编剧创造出一个故事,但决定怎么将它拍出来的是导演——这正好像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的关系。我们喜欢故事,小时候趴在床头听妈妈讲故事,长大了靠在沙发里看小说和电影。故事的情节一环扣一环,但我们所得的不是规律,而是一种模糊的快感。
对于讲故事的人来说,如今的这个时代给他们提出了最严苛的要求。在马洛和莎士比亚的时代,一个普通观众一周能有多少时间在故事中度过?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们每天都在报纸、书本和屏幕上看到大量的故事,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他看到的故事完全是陈词滥调,这是对故事讲述者最严厉的批评。我们交出时间、耐心和想象力,配合故事讲述者一起奔赴那个想象中的美丽终点,如果他将我们带上一条死路,我们会失望透顶;如果有人在中途告诉我们故事的结局,我们就会感觉道路被突然切断,暴躁愤怒。我们同样无法容忍故事被打断,《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里收录了一个俄罗斯民间故事,叫《丈夫如何让妻子戒除故事瘾》。一个客栈老板的妻子迷恋听故事,只招那些会讲故事的人当房客。丈夫十分苦恼,一天晚上来了一个老头儿,答应讲一夜故事,但条件是任何人都不能打断他。结果老头儿一直讲:“一只猫头鹰飞过一座花园,落在树干上,喝了点儿水。一只猫头鹰飞过一座花园,落在树干上,喝了点儿水。”妻子忍无可忍,抱怨老头儿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东西。结果老头儿说:“你为什么打断我,我后面会有变化的!”丈夫就从床上跳下来痛打妻子,埋怨因为她的打断老头儿再也不肯讲故事了。妻子一生气,以后就再也不要听故事了。
这个故事来自口头讲述的文学传统,逻辑上不是很严密,人物性格也不鲜明,但它却触及了人类与故事的几点最本质的关系。它首先提示我们,人类会对故事上瘾,《一千零一夜》里的山鲁佐德正是靠着这种瘾成功拴住了暴君的心;同时它也暗示,故事在诱惑的同时具有某种禁忌的力量,我们对于讲故事者要有足够的尊敬和耐心。人类对故事着迷已久,公元前19世纪到前16世纪,世界上最早的叙事史诗《吉尔伽美什》就已经成文,吉尔伽美什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最终追求永生而不得。如今几十个世纪过去,类似的故事依然在被讲述着,哈利波特在寻找死亡圣器,弗罗多在寻找魔戒。全世界每年所有的出版物中,叙事类作品的数量比其他所有类型的书加起来还要多。学者们乐于分析故事的各种母题,前苏联学者普洛普甚至把神话故事拆解成31种功能,并宣称已经研究清楚这些功能分解和组装成不同故事的秘密,但值得惊叹的是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从单调而有限的母题中生长出来的故事一点都没有呈现出要衰竭的迹象。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高察尔写了一本《人类:讲故事的动物》,他说世上所有的故事就如同所有人的面孔,看上去都差不多,但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这些面孔后面隐藏的记忆,恰如同故事背后的故事,永无止境。
乔纳森•高察尔说,故事对于人来说就像水对于浮游生物,你感觉不到它,但你总生活在其中。一项调查显示,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会花20分钟在阅读上,但同样的一个人每天都会看几个小时电视,加上去电影院的时间,他每年可以计算的花在故事上的时间至少在2000小时以上,这还没算上在地铁、公交上等待、以及在工作中走神的时间。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像是人从虚空中偷来之物,用于供白日梦驰骋。在移动上网设备和微博流行的时代,我们越来越难集中精神,每天要走神两千多次,每次大约14秒,正好够一个故事展开。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些故事发展得远比纸上迅速。但我们毕竟能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那些我们意识不到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叫它们症状。晚上是人类故事创造力最旺盛的时间段,无论是美梦还是噩梦,它们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越我们在白天经历和阅读的那些内容。即使最厌恶故事的人也不能避免做梦,这些梦正是以故事的形式构建起来的。我们在白天的那些无趣的、挫败的、希冀的、渴望的经验,在睡梦中以目前明朗的方式被拆散变形后重组。我们自己经历一遍,然后弗洛伊德再用他的理论重新构造一遍。和那些纸面上、银幕上的故事一样,在这些梦的深处,也是欲望在左奔右突,映射出我们内心的秘密。故事天才要做的事是和梦类似,他面对的是我们日常的经验,要将其转化为更清晰、更有力也更曲径通幽的的方式,他在琐碎的、看似无序的生活的界限之外画出了一条路,通向爱丽丝和孙悟空的奇幻世界。他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造物主的工作,和无数的故事讲述者一起,他建造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岛屿。起初人们还喜欢在故事里提到“有个遥远的地方”,后来他们觉得这样太幼稚,对故事发生的地方绝口不提,最好让人觉得它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亚美尼亚的口头文学传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他们通常这样开头:“在有与没有之间,有一个男孩……”
人类能想象未来,知道一些事和另外一些事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构建和理解故事的前提。这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与故事保持步调,在其中进行想象力和社交的模拟飞行。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孩子们特别爱听故事,因为其中有太多他们未曾经历之事。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里头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与此有关的经验倒错,中国皇帝从小在深宫看着画师王佛的画长大,认识万物皆有赖于此,但他二十岁那年走出深宫,发现现实远不如绘画那么美:“朕登上皇宫的平台,观看云彩,发现比不上你画的黄昏那样美丽……朕周游各省,都找不到你画的那样的花园……也没有找到你画的那些女人,她们的身体就和一座花园一样。海岸边的石子使朕对海洋产生厌恶;你画上的石榴比受刑者的鲜血更红;”皇帝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并不能伸展到那“遥远的地方”,于是想将王佛处死。但王佛最后画的那片大海成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老画家和他死而复生的徒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画中消失。讲故事的人握有豁免权,读者不能要求他们为故事的后果负责,包法利夫人和堂吉诃德那样的失败读者也没有权利找到小说作者要求他们赔偿。奇怪的是,人们在对待理论知识的时候会谨慎得多,卢梭写了一本《爱弥尔》大谈儿童教育,可是没有人照着他的方法去教育自家的孩子。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害怕感性经验侵占了说理的空间,要把游吟诗人驱逐出境,而一直以来故事带来的感性经验在我们的世界里的地盘只会越来越大,托尔斯泰会写故事来传播道德,希特勒会焚书来统一思想,它们甚至在改变历史。林肯见到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斯托夫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喔,你就是那个写了本书引发了南北战争的女人。”
如今越来越多的故事在屏幕而不是纸上出现,这种改变像印刷术对书的塑造一样巨大,但我们似乎不需要经过什么训练就能接受它们,然后参与到继续塑造它们的过程中。1944年,美国心理学家海德和西美尔做了一个没有情节的动画短片用于心理学实验,其中的三个角色分别是运动的三角形、方形和圆。他们向参加实验的114人询问观看动画片的所得,认为这是一个三角恋故事的人有111人,其余3人答只看到了几何图形的运动轨迹。法兰克福书展“故事驱动大会”的论坛试图融合出版业、电影业和游戏业对于“故事”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举办了三届,今年的头一场演讲上,这个动画片又被重新播放,现场依然有绝大多数人以为它是个抽象的肥皂剧。屏幕上的故事比纸上的故事更有产业价值,这不是新鲜事,麦基就对有些作家非常不屑,因为他们的作品在银幕上没有价值。在故事领域,摄像技术对印刷术的优越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现在更先进的电脑技术正在崛起,EA在2011年推出的电脑游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讲述了一个反恐故事,玩家扮演美军和英军士兵,在世界范围内挫败来自俄罗斯的军火巨头的阴谋。这个游戏在发售的第一周内就创下了7.75亿美元的纪录,销售业绩超过了詹姆斯•卡梅隆的巨作《阿凡达》。一些热爱书籍的人可能看不起电脑游戏,认为它们情节简单,玩游戏的人都是些宅男和极客,进入不了主流社会,但去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尼基•哈利也在奥巴马演讲的时候拿iPad玩起了《愤怒的小鸟》。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作家萨尔曼•拉什迪都是这款游戏的老玩家。《愤怒的小鸟》虽然玩来玩去只有一个动作,但每个系列都有自己的情节,还和20世纪福克斯合作拍了一部叫《里约大冒险》的电影。这是一个趋势,现在的游戏已经不是“吃豆人”和“俄罗斯方块”那么单调了,他们都具有一个故事作为内核。复杂一些的游戏更加重视故事的力量。从2005年至今,《魔兽世界》一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网络游戏,它有一个类似《魔戒》那样非常宏大的故事背景,创造了一个叫“艾泽拉斯”的虚拟世界,还出版了官方小说。这个“大故事”还会不断繁殖,上线不久的资料片《熊猫人之谜》就是一个全新的产物。玩家们也会根据这个大背景自己写同人小说,网上到处可见这些业余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还得到了出版。
菲利普•罗斯抱怨二十年之后的小说会像今天的诗歌一样没人阅读,但事实是故事不会死亡,它只是找到了新的领域。退一步讲,小说也不会死亡。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小说家可以赚到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同行都多的钱,罗琳、保罗•科埃略、甚至马尔克斯都有上千万的读者。人们曾经通过口头和写在纸上的故事得到的那些经验和快感,如今依然存在,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可以在游戏里得到更多。《阿凡达》的故事也是一个人操纵他的虚拟自我冒险的故事,这十分类似游戏体验。故事的边界和影响力都在扩展,索尼公司在PS3上发布的游戏《暴雨》被誉为新时代的《公民凯恩》,玩家要操控不同的人物,找出谜案后的凶手,他要分别扮演受害者、记者和杀人魔,替他们做决定,让他们行动,无数分支都会导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形成的合力将会影响游戏结局。这种即时性的体验使得参与故事的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复写它,导演、演员和观众成了一个人,故事更好玩儿了。乔纳森•高察尔是最近一次“故事驱动大会”最重要的嘉宾和发言人,在他看来,故事和虚拟体验尤其是网络游戏的结合具有无比广阔的空间,故事的未来就蕴含在其中。这是新的经验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在其中扮演、书写、体验,只要给定一个空间,人们的创造力就能在其中发挥,哪怕是在虚拟世界里,精于故事的人也会得到更多的钱,其他人则能收获快乐。这听起来有那么点儿不切实际,当世界停电的时候怎么办?不只是停电,这个世界还会贫穷、混乱甚至爆发战争,但那个“遥远的地方”不会,不管地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永远就在那里,精彩又安宁,像宇宙一样永恒。
七故事——
每个人在16岁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刻骨铭心的伙伴,库比泽克也一样。那个晚上他和朋友阿道夫去林茨看瓦格纳的歌剧《黎恩济》,在楼顶的廉价座位消磨了5个小时。散场后他们一起走回家,阿道夫忽然停下来抓住他的手说:“这部歌剧让我无比感动,总有一天我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戴,把他们从苦役中拯救出来!”,说完就很悲壮地往前走,弄得他不知所措。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去给别人扫雪赚点零花钱,完事后到邮局蹭暖气,在那儿阿道夫又说他要考艺术学院学绘画。这是库比泽克最后一次见到这个朋友。后来学校没录取他,他那些风景画作只有游客才愿意花点零钱买。几十年后阿道夫带着他的瓦格纳唱片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库比泽克才知道黎恩济之夜是多么意义重大,从那开始他就再也没能赶上朋友的步伐。他听见阿道夫•希特勒穿着纳粹军服说:“我愿意在瓦格纳的乐队里当一名鼓手。” -- 改写自库比泽克的回忆录
一定有人想谋害萨达姆•侯赛因。有一天早上两个从未见过的人来敲门,说一宗不应属于他的大宝藏埋在他家地下。邻居们平日无聊,听说这样的新鲜事都十分兴奋,用异样的眼光看他,都说从美国来的穿黑色西服的人决不可能说谎。侯赛因十分苦恼,因为他不可能掘地三尺自证清白,那样倒可能会挖出什么不知来由的陈年尸骨来;他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因为那两个黑衣人成天不怀好意地在家门口游荡。日久天长,他想起自己一生别的罪行,不免有些松动。后来黑衣人把他架到市场要绞死他时,他的灵魂飘到了街边叫好的人们一边。他在人间最后的记忆是看到远方窗子里有个黑影,向他伸出双手好像要说什么,但随后他的意识就如同灰尘般飞散了。那个窗子里一个总统拿着一纸文件对另一个说:“他家里就是有宝藏。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不同的看法只反映了人们的困惑。” -- 改写自卡夫卡《审判》
时常在美国杂志上出现的本•拉登的照片并不是他本人。他是家里第17个孩子,藏身在厚厚的族谱和一大把胡子后面。他发财的门路很多,在一个地方钻出石油,再到另一个地方卖掉,只不过是小把戏之一。本•拉登大半辈子都在和苏联、美国为敌,人们说他是最不怕死的亿万富翁。美国以外的人们恨他,但也不那么恨他,他的白色头巾与阿富汗山区的石头一起提醒着人们全球化之前的时光,于是当他的人劫持了飞机撞上纽约的大楼时,还有些看热闹的人叫好。后来本•拉登没有得到什么机会,他不得不像崇拜过的先知一样远离世界,躲在地球褶皱的一个二层小楼里,电脑硬盘里存了不少色情影片。最后他焚烧垃圾的烟雾引起了邻居的嫌恶,他们叫来美国大兵打死了他。不远处一只老迈的山羊见证了这一过程。 -- 改写自博尔赫斯《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
车开到塞纳河边的时候,我低头发现上衣有一粒纽扣松了,那是在胸口下方几厘米的地方,它不松不紧地悬挂着,像是一个随时要落地的水滴。我嫁过人也离过婚,但从来不会做针线活,我们城堡里走出来的人不需要会这些,我们的衣服永远像走廊里挂的油画那样永远平整无暇,即使上面蒙尘,老去的也是人而不是衣服。我似乎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关心琐事的环境里,可是我能控制什么呢,我的纽扣会掉下来,就像查尔斯会在某个地方拥抱卡米拉,或是远处一个地雷忽然爆炸,我们是“高贵”的灰尘吗?在某个角度看,这个纽扣像是整件衣服上突起的一个部分,如果它有生命,它是想脱离什么吗?我从来没有脱离过什么,我身上的衣服越来越重,啊,后面的车一直在跟着我,他们从哪儿来?报社还是军情六处?司机,你能开快一点吗?我们到哪了?进隧道了,一切都暗下来了。 -- 改写自伍尔芙《墙上的斑点》
从前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学生痴迷计算机,有时候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不出门,就为了黑一个网站。后来他的亲人们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有这时间当黑客还不如去多认识几个有钱的同学,有钱人才能带给他好运。他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去,结果人们发现他一到社交场合就絮絮叨叨,说的话几乎没人愿意听。他去过不少舞会,也参加了不少会议,不管是男是女,人们都对他嗤之以鼻。后来终于有两个富家子弟找他在技术上帮点忙,他就很激动地和他们倾诉了自己靠网络发大财的梦想,结果富家子弟哈哈大笑:你又不是比尔•盖茨,人家设计了一个操作系统!我们俩这次找你来是打算弄一个哈佛关系网,让大家方便交流,居然有人荒唐到想靠这种类似通讯录的东西赚钱?有谁会那么傻把自己的隐私放上来给你玩?这个学生听了他们的话,就很认真地开发了哈佛关系网,最后做成了社交网络。 -- 改写自《一千零一夜》
全国的有钱人都生了一种怪病,他们控制不住自己,想要和更多的女人睡觉。他们先是去找妓女,然后被妻子发现,最后花费好多家产离婚。伍兹先生是他们中最倒霉的一个,除了在电视上道歉外,他丢了几个世界冠军,背上还长了一个瘤子。这瘤子一天比一天大,这令他非常苦恼,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能仰着睡觉了。国王就找来全国最出名的医生研究伍兹先生的病,只要治好了他,全国有钱人的病也迎刃而解了,毕竟他们是国家的支柱嘛。医生们废寝忘食地辩论和做实验,最后得出结论说伍兹先生的瘤子是传染源,它散发出的病菌感染了大家。国王下令把瘤子切掉,结果医生刚剖开外皮,里面就跳出来一个和伍兹先生一模一样的人,带着伍兹在原地转了几圈,这下大家就分不清谁是真的伍兹先生了。大瘤子说起仁义道德来比伍兹先生熟练多了,医生们断定真的伍兹先生是大瘤子,把他切碎扔进了垃圾箱。解决了传染源,富翁们和国王都放心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新的伍兹先生非常聪明,他甚至学会了打高尔夫球,排名已经追到世界第二啦。 -- 改写自《关于来洛尼亚的十三个童话故事》及《南方公园》第十四季第一集
这些日子人们对辩论的兴趣大为淡薄了。从前有段时候辩论家们一见面就开始谈论哲理和公义,周围就迅速围拢来一大堆观众。那些更加义正言辞的人因此变得富裕。但后来市场萧条,辩论家们另谋出路,导致这个行当渐渐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人们来看他,通常是因为他当年的名气,但他找不到人辩论了,可观赏性大大降低,他的生活境况也越来越差。他对观众们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辩论艺术,这里面蕴含了哲理和公义。”围观的人们都慵懒地表示很赞赏。“但你们不应该赞赏,因为我除了表演辩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已经疲惫,转向了辩论家不远处的另一个舞台。“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身份,假如我找到这样的身份”,辩论家的瞳孔在放大,眼神里流露出坚定的信念,“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在微博上谈论天气和宠物,永远开开心心的。”后来人们尊敬地把他埋了,相信辩论家们也许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推动了历史,然后就什么都忘记了。 -- 改写自卡夫卡《饥饿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