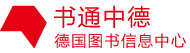媒体中心

刘震云:我是中国最绕的人
北京晚报, 1999年11月30日
“本来我这部分开场的时间是五点,结束是六点,我一看现在已经快六点了。这是一个幽默,特别符合文学的特质,从结束的地方开始。就好像声音停止的地方出现了音乐,色彩停止的地方出现了图画,生活停止的地方就出现了文学。”5月29日下午,由法兰克福书展和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故事驱动中国”大会,邀请了著名作家刘震云,和现场观众分享他对于故事、文学和电影的思考。不到一个小时的讲述中,刘震云妙语连珠,幽默而真诚的发言让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中国的生活太幽默
故事驱动中国这个题目,有意思。一个民族是故事在驱动着,整个世界也是故事在驱动着。有三个故事驱动着地球的转动,一个是耶稣的故事,一个是穆罕默德的故事,一个是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们对于世界的推动的特点是,都是破壳的故事。这三个伟大人物的出生,跟我们的理解就非常不一样。非常出格的三个故事在推动这合乎规则的世界转动,这是故事的本质。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最绕的人。还有一个对我的定位是,我很幽默。其实我是最不幽默的人,是因为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让我这个最不幽默的人显得幽默了。绕出来一句话就是,真实最幽默。
我首先说说作者在创作道路中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首先都先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作者都是这样,接着,会离开自己,试图走得更远。转了一圈,他发现又回到自身,但是这个自身跟他一开始写的自身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圈看似是转回来,其实已经转到了另外的地方。
写实在文学中是永远不存在的,如果你写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样的,那这个作品没有人看。最大的不一样,可能是你对生活理解的不一样,细节可能是窗外发生的细节,但是你的理解跟窗外是非常不一样的。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作者对待文学和生活的态度。
有两种作者,一种作者他个人的风格越来越明显,作品中的自己越来越突出了,比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还有一种作者写得越来越没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见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的作品。我喜欢的是后一种。
其实我还想写一个《我不是西门庆》。再之后我想写一个人物,就是三十年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通过三十年,怎么变成老林了。因为三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特别单一,是一个权力社会。三十年后中国的社会特别的纷繁,除了是个权力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金钱的社会。权力和金钱杂交之后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的单元、各种圈子、各种阶层。我们经常从媒体上能够看到,海南发生了好多富二代和官二代的party,这个party上有很多女孩子是不穿衣服的。官二代和富二代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觉得他们是在制造一个工具,左钉一块板子,右钉一块板子,最后钉成了一个方块,就差往里边躺了,叫作“棺材”。中国近三十年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一定是街上挤公共汽车的,由小林变成老林的,三十年所有工作的负担压在了这些人的身上,他们依然是有着憾事,他们看到官二代和富二代新闻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中国人的孤独与西方人不一样
文学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说是讲故事用的。但是刘震云的东西,主要不是讲故事用的。文学是一种思考。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思考生活中存在的哲学问题。
比如《一地鸡毛》,其实是在讲大和小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八国首脑会议重要,可是主人公小林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家的一块豆腐馊了。这是一个哲学道理。比如《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一个芝麻怎么变成了西瓜,一只蚂蚁怎么变成了大象。
《温故一九四二》,讲的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其他民族面对苦难一定要追问,是谁把我们饿死的。一场旱灾,在我的家乡饿死了300万人,什么概念呢,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110万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追问,但是我们河南人临死的时候,却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幽默。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我比你多活三天,我值了。
其实外国的读者能不能读懂,我作品里写的孤独感这个问题,《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讲一个区别:中国社会是个无神社会,我们对神和鬼有极大的功利性,凡去庙里拜佛的,一定是有事相求。但是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最大区别不在功利上。而在于,有神社会想找一个朋友诉说心事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上帝、找真主、找佛祖。上帝最大的特点是嘴比较严,我找上帝忏悔,上帝一定可以原谅我。但是在无神社会,你如果想把自己的话说出来,一定要找一个知心朋友,而朋友跟上帝最大的区别是,他可以把你说的话告诉别人。
所以说中国人的孤独和西方人的孤独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孤独是倾诉之后的孤独,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倾诉的孤独。中国人一般上吊的人都是憋死的。
《一句顶一万句》里有一个意大利的神父,他来中国40年,传教只传了八个徒弟。他特想把一个我们可以有心事对他说的朋友带到我们身边,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朋友是多余的。他在黄河边碰到一个杀猪匠,神父劝他信主。他说为什么?神父说,你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杀猪匠说,不信我也知道,我是个杀猪匠,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作品是不是被其他文化所接受呢?我看也接受了。《一句顶一万句》法文版10月份就能够出来,英文版、韩文版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包括阿拉伯都会陆续的出来。但是几个语种的翻译倒是共同给我反馈过一个意见,说,为什么你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多,有名有姓的上百个。能不能以后写作品有名有姓的不超过五个人?我觉得这也是中西的区别,他们忽略了,确实我们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第二,所有的翻译都建议我改一下名字,刘震云这三个字不管是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包括阿拉伯文读起来特别的拗口!我要是早改成莫言,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笑声)
哲学驱动电影
首先我不是个著名的编剧,我的小说写得吧,非常好(笑声),但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因为我把剧本当成小说写了。去年冯小刚导演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了电影。他在拍摄期间最大的苦恼是,我的剧本里老是出现八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逃荒的队伍、中国的军队、日本的军队,都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要花很多钱!制片人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我的剧本写得太长了,拍出来的素材能剪十个小时。但是影院里要求,像冯导这样的大牌导演也不能超过两个半小时。
得出来的经验就是:好的剧本不要超过1500字。我对冯导说,下次写剧本的时候就写两页纸,用文言文写。
《我叫刘跃进》是马俪文导演的作品,她是位非常有才华和见识的女导演,长得也很漂亮。之前拍过一个特别优秀的电影《我们俩》,她特别能够掌握一个电影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狼和羊的关系。世界上都知道狼是要吃羊的,但是她通过这个电影告诉大家,羊有时候也可以吃狼,因为羊太多了。这个电影的缺陷是投资太少。高群书最近一部作品我很喜欢,是《神探亨特张》,把一个警察片拍得那么深情,那么流畅。
《一九四二》接连得了很多奖。冯导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电影坚持19年,不容易。还有如果大家看过《温故一九四二》,这是最不适合改编电影的小说,因为里边没有任何的情节和故事。如果故事是驱动电影最主要的因素的话,它是零。但他为什么还要改编成电影?他一定看到了大家认为重要东西背后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特别想写一部悲剧,但是里面充满了笑声。这是一个哲学观点,一句伟大的话。
冯导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对演员辅导,情感一定要节制,死了300万人,告诉演员不许哭,要让观众笑。所以我在首映式上看到大家在笑,我感到很欣慰。笑完之后观众自己不好意思,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要让我们的民族不好意思一次,这是写《一九四二》最重要的目的。就像灯光一样照亮了我们这个民族黑暗的一角。
伊朗人和保定人没有区别
另外我要说一个老电影《教父》。我认为《教父》是影史上登峰造极之作,科波拉在拍《教父》时,每天都面临被制片人炒掉。而且《教父》里有很多穿帮镜头,他把亲戚朋友都塞在片里,他爸妈、他二姨、三姑、他女儿都在里边。
但这部电影伟大,不在电影的题材,而在于里边有一套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么暴力的电影,其故事的驱动力和发动机是什么?我觉得科波拉的水平都快接近我了(大笑),他是个哲学家。一个特别恨的电影,驱动力和发动机是爱:每次杀人,每次黑帮火并,包括自己家族内部人的暴亡,没有一个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爱。《教父》看到最后,新教父对其他帮派进行清理,我们的情感站在小儿子一边,觉得特别解恨。我觉得哲学驱动电影,也驱动中国和世界。只懂故事,不懂哲学的编剧是非常平庸的编剧和导演,这样的人占90%。
很多人说电影从文学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就我体会是文学也从电影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电影跟文学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故事和人物,而在于时间。电影院像餐馆一样希望客人早吃完早走翻台,电影120分钟里要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见识讲出来,和20万字讲出来是不一样的。它的对话要非常精粹,如果搁到小说里,你的小说质量会极大地提高。电影的审查比文学严,也是因为时间。90分钟、120分钟可以看一个电影,审查容易,看书太麻烦。所以文学比电影宽松。
什么样的故事既能让国内也能让国外读者欢迎,很简单,感人的故事、人性的故事。民族和民族间确实有差异,但是在最根本问题上,比如爱和恨,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亲戚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各个民族都一样,都是因为男女关系产生的,这就是爱和恨的根本,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人类感情的背后,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在CNN里边,伊朗是个特别古怪的国家。但是当我们看了《小鞋子》和《一次别离》,我们就发现伊朗人跟保定人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一双鞋在整个的家庭中起的波澜,一次离婚跟德黑兰发生的事与北京、石家庄没有任何区别,这是艺术家对这个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伊拉克没有产生这样的电影,美军轰炸伊拉克和轰炸伊朗在我心里引起的波澜是不一样的,伊朗我有亲戚,我想轰炸的时候《小鞋子》里的小姑娘会怎么样,《一次别离》夫妻俩会怎么样,这是他们的电影走向世界的最根本原因。
问答
问:你怎么看待莫言得诺奖?
刘震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老莫得奖之后,我接受的采访不比他少。好比我哥娶了个媳妇,洞房花烛夜,问我的感受,这都是居心不良的人。说话过去大半年了,我的标准回答是:祝我哥愉快!当然了接着有人问,好像你也快到结婚的年龄了?我的标准回答是:我不急。一个奖项可能会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这个奖给得奖的人带来了什么,还有一种是这个人给这个奖带来了什么,我希望我是后一种人。
问:从好故事到好电影大概有多远,有几个步骤?
刘震云:永远有多远,它就有多远。(笑)并不是这个故事到达电影有多远,它近在咫尺,关键是找到一个干这个事的人,这个路程是非常非常远的。现在不好意思的人多,脑子像一盆糨子的人多,明白人少。
找什么样的人,包括找朋友,找对象,特别简单,要找一个明白人,什么叫明白人?就是有见识的人,什么叫有见识的人呢?认识跟别人不同的人。什么是认识跟别人不同的人呢?就是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人。这种人在世界上很少。中国人不缺钱,就缺远见。你找一个有远见的人,一个人做事看十天和看一年,看十年,看一百年,做事的出发点和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问:您的电影是把人物还是故事放在首位?
刘震云:把见识放在首位,有见识的话我觉得人物和故事已经不重要了。电影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同一篇作品,能得第二次稿费。这个稿费对于一个自由职业者来说,能够反哺文学。一个作者,一个民族那么优秀的作者,应该让他保持起码的体面和尊严。不然他会使这个民族很不好意思。这个体面和尊严是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而不是像那些专业作家一样,是拿纳税人的钱来的。如果一个写作者另外拿了纳税人的钱,也让我不好意思。
(资料来源:点击这里)